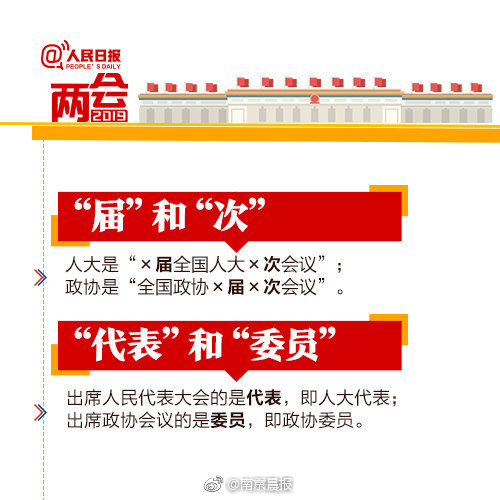臭脚女混混给我打脚枪的真实经历,校园往事不堪回首,那段被欺凌的
当地时间2025-10-18
初遇“臭脚团”,噩梦的开始
中学二年级那年,我们班里转来了一个叫小雅的女生。她个子高挑,皮肤略黑,总喜欢把校服裤子卷到脚踝,露出一双脏兮兮的白色运动鞋。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总跟着三四个女生,她们自称“臭脚团”,因为总不换袜子,走路带风时确实能闻到一股酸臭味。但没人敢笑话她们,因为她们是全校出了名的小霸王团伙。
我性格内向,成绩中等,是那种老师记不住名字、同学也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学生。本以为能安然度过中学生涯,却因为一次值日时的偶然冲突,被小雅盯上了。那天我拖地时不慎把水溅到了她的鞋上,她当场踹翻了水桶,揪着我的衣领说:“你等着,这事没完。”
从第二天起,我的噩梦正式开幕。她们把我堵在厕所、楼梯间,甚至放学后的小巷子里。起初只是推搡和辱骂,后来变本加厉。最让我恐惧的是“打脚枪”游戏——她们逼我跪在地上,用脏鞋底踩我的脸,还必须大声数着“一枪、两枪……”。若数错了或哭出声,就会换来更狠的踹踢。
那段日子,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胃绞痛。
我曾试过告诉班主任,但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女生之间打闹很正常”。父母工作忙,见我成绩没下滑,也就没多问。我渐渐学会沉默,在日记本里写下:“今天又被打了七枪,左边脸颊被鞋印磨破了皮。”
扭曲的“规则”与无声反抗
“臭脚团”甚至给欺凌制定了规则:每周一、三、五是“固定游戏日”,而我需要提前替她们写作业、买饮料作为“参与费”。她们用手机录下我的窘态,威胁说如果我不听话就把视频发到网上。现在回想,那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游戏——通过羞辱他人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奇怪的是,我居然慢慢习惯了这种扭曲的生活节奏。甚至开始研究如何让她们“踩得轻一点”:比如故意穿厚外套减少疼痛,或者提前在口袋里藏好纸巾用来擦脸。这种可悲的适应力,如今想来让人心酸。
转折点发生在一次体育课上。我们班和隔壁班打篮球赛时,小雅意外扭伤了脚踝。所有人围着嘘寒问暖,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她单脚跳着经过我身边,突然低声说:“喂,扶我去医务室。”那一刻我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用近乎正常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鬼使神差地搀住了她的胳膊。路上她突然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校长?”我苦笑着反问:“说了有用吗?”她沉默了很久,直到医务室门口才嘟囔了一句:“其实我们以前也被这样欺负过。”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脆弱。
真相与和解的曙光
那次意外之后,“打脚枪”游戏莫名停止了。小雅依然带着她那帮姐妹横行霸道,但不再针对我。有时甚至在走廊相遇时,她会对我微微点头。后来我从其他同学那听说,小雅初中时曾被高年级学姐长期欺凌,甚至被迫舔过别人的鞋底。“臭脚团”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是她对过往创伤的扭曲复制。
毕业前最后一个月,学校组织了一场反霸凌主题活动。在匿名倾诉环节,我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没想到的是,小雅竟然也提交了一张纸条:“我曾经伤害过一个同学,因为我觉得痛苦就该传递给更多人。现在我知道错了。”
活动结束后,她在操场角落拦住了我。我们第一次平等地对话。她说:“那时候觉得你软弱好欺负,就像当年的我。但你知道吗?你比我们任何人都坚强——至少你从来没有变成欺负别人的人。”她顿了顿,又说:“你那会儿数‘脚枪’的声音,其实每次都在发抖,但从来不会求饶。
”
那一刻我突然释然了。原来在这场扭曲的权力游戏里,她始终注意着我的抵抗——哪怕只是沉默的、颤抖的抵抗。毕业典礼那天,我们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拍了合照,她没有笑,但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张照片我至今留着,背面写着一行字:“致不曾屈服的我们”。
走出阴影,拥抱光明
现在回想那段经历,我依然会心悸冒汗。但时间给了我新的视角:校园暴力中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施暴者用伤害他人来掩盖自己的伤口,受害者则在多年后仍需与PTSD抗争。去年同学聚会时,我听说小雅去了南方打工,曾经嚣张的“臭脚团”成员大多碌碌无为。而我从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成为青少年心理咨询师。
每当面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我都会告诉他们:“疼痛会过去,伤疤会淡去,但你选择不变成施暴者的那份尊严——永远闪光。”去年冬天,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写着:“对不起,谢谢。”我猜那是小雅寄来的。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已经发生。
这段往事教会我:黑暗的经历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解药。如今我能够坦然谈起“打脚枪”的故事,不是因为伤痛已消失,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当年那个数着“脚枪”却不肯哭出声的少年,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握着拳头。
星辰甘源食品(002991)6月30日股东户数1.04万户,较上期增加2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