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11-11,rrrrdhasjfbsdkigbjksrifsdlukbgjsab
核心提示
秋日的大连艺术学院校园,天高云阔。1号演播厅内,学生们用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演绎着原创作品《山蝉》。台下就座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神情专注,不时露出欣喜。提问环节,年轻人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的颤抖,他亲切地将其拉到身边,言语里满是鼓励……这是9月28日濮存昕参加辽宁省第十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场景。
活动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专访,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岁月虽然带给这位72岁的表演艺术家以鬓白,但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使他依旧充满了活力。他将自己对生活、角色、人性的观察与探索,酝酿成哈姆雷特、索尔尼斯、李白、鲁迅等一个个经典形象。与这位点亮舞台的掌灯人对话,我们得以看到他深邃饱满的内心世界。
“大学生戏剧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
本报记者:刚刚您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分享一下感受吧。
濮存昕:戏剧助你理解世界认识人生建立审美。面对孩子们,我发现很多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青春的气息,年轻人如何看待事物、看待艺术等等。看了汇报表演后,我也在判断,我还是否拥有像他们那种返璞归真的能力。所以,要不断尝新。对于戏剧发展而言,我们要传承传统,做到老而不旧。创新不仅仅是形式方面,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力的注入。
今天,我在大艺课堂的孩子们身上又发现了自己最初在业余小队时候,在田间地头的那种表演冲动。他们很有灵气,比如《山蝉》的编排,就很智慧,用一条红皮筋这样简洁的方式构建人物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
本报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戏剧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濮存昕: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从初绽的蓓蕾成长为辽宁文化版图上枝繁叶茂的艺术品牌,托举着辽宁文化新生力量的滚烫理想。它真正的意义就是促进教育。大学生戏剧节不要追求专业化,不要追求高成本的制作。这次大学生戏剧节上除了有艺术院校学生的汇报,还有很多人来自非艺术专业的学科,他们热爱表演。我相信,舞台上精彩表演的瞬间,真的就是人刹那间的真情流露。那是一个神光乍现的时候,不可言说。
本报记者: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是您觉得还没演够的?
濮存昕:有,但没有机会演了。比如我演过易卜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建筑大师》。我在索尔尼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感受到建筑师对生命和责任的彻悟与困惑、幻灭与热爱、恶意与温存。说实话,没演够,越琢磨越有滋味。
江南水韵:西施的秘密
提起江南,总能让人联想到那缠绵如水的风景与细腻如诗的文化。这里,有潺潺的小河、静谧的水巷、杨柳轻拂的码头,而这一切的美丽背后,藏着一段关于绝世美人的传说——西施。她被古人誉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样的容颜仿佛天生带着淡淡的诗意,令人难以忘怀。
“西施诗語江南脸红流白水”,这句话犹如江南的风,轻轻拂过心头。西施的笑颜如同江南的桃花初绽,脸颊泛红,仿佛含苞待放的花蕾,又似晨曦映照下的桃红。她的美不是耀眼的高调,而是一种静谧中的婉约,一种水中倒影般的淡然,从容而深邃。坐在江南的水巷中,无数诗人用笔描绘她的柔情,吟诵出流传千古的诗句:“脸红流白水”,像是描述那水面泛起的涟漪,又像是在描绘那脸庞上的恍若桃花的娇羞。
江南的水,轻柔细腻,仿佛是天工开物的杰作。她柔和地流淌在青石板路之间,映照出西施如水的温婉。古人说:“江南水乡的女人,若是脸红了,便如白水泛起层层涟漪,轻轻摇曳。”這细腻的比喻,将美人的心境与江南水的柔和完美结合。西施在那水的映衬下,不仅是一个绝世美女,更是一幅活生生的江南畫卷。
在江南的诗意世界中,西施的出现仿佛是天赐的恩赐。她的美丽超越了凡尘的繁华,仿佛从湖水中倒影而出的一首诗,清新婉约,令人心醉神迷。她脸上那一抹娇羞染红了江南的春水,也融化了许多人心底的坚硬。每当春风拂面、细雨蒙蒙,江南的水面就会泛起微微的涟漪,好像在为西施的娇颜起舞。
这种情景,既是视觉的盛宴,也是心灵的洗礼。
当然,西施的美丽还隐藏着一种深邃的智慧。一如江南水乡的宁静,她的美不仅仅是外表,更是一种温和、谦逊、善解人意的内涵。她的笑容轻盈如水,温暖如春日的阳光,脸红時如桃花映红了江南的水面。那些流淌的白水,似乎在诉说着她温婉婉约的情感,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诗意。
江南的水,孕育了许多关于西施的传说和诗篇。在那些诗句中,她既是江南的象征,也是那一抹令人心动的美丽华章。与其说西施是江南的姑娘,不如说她是江南水乡的灵魂。她脸红流白水的模样,早已成为古今文人描绘江南的最佳写照,也成為最美的梦境,让无数旅人心驰神往。
诗意人生:从西施到江南的美学追寻
走入江南,仿佛步入一幅流动的画卷。这里的每一座古桥、每一条石巷、每一片水草,都在讲述着属于江南的静谧与柔情。在这片水乡大地,西施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位美女的写照,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关于美的极致追求。
“脸红流白水”作为极具画面感的诗句,反映了江南女子那份含蓄、柔和而纯净的气质。这种美,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浮华炫耀,而是如水般清澈、如云般飘逸,是一种超越外表的内在气质。江南的美学正是如此,它追求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境界,而西施正是这一美学的最佳符号。
人们常说:“江南女子如水,脸红如桃花,流白如江面上的涓涓细流。”这既是对她们外在的赞美,也是对那份宁静、柔弱中隐藏着坚韧的美的歌颂。西施的美,将江南的文化精神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她的眼神如水,輕盈;她的笑容似花,娇媚;她的脸颊泛起的微红,像刚刚绽放的桃花,令人心生怜愛。
江南的女子,会用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展现出她们独特的韵味。
西施的传说与江南的诗意风情相辅相成。无数文人墨客在吟咏佳人时,用流水、桃花、白水、红晕等意象,勾勒出那份动人心魄的美丽。她们的脸,红得恰到好处,像桃花泛红;她们的肌肤,白得如江水般清澈,仿佛可以一眼望穿。站在江南的小桥上,面对那一池碧水,心中总会升起一股淡淡的情愫——那是对理想中美的追求,也是对生活之美的敬意。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江南的美学依然如一股清流,洗涤着浮躁的心灵。许多现代人追寻那份“脸红流白水”的柔和与婉约,无论是穿着、生活方式,还是精神追求,都在试图找回那份纯粹与美好。江南的水,仍然静静地流淌;西施的影像,也在时光中逐渐变得越发深邃。
這份美丽不拘泥于外在的繁华,更体现于心底的安宁与从容。
走在江南的小巷子里,望见那一片水天相接的画卷时,心中总会泛起一阵暖意。那是属于“脸红流白水”的江南情调,也是对美好生活最深刻的向往。或许,真正的美丽,正藏在这些细腻的瞬间里——如水,静静流淌,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本报记者:您导演的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将前往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国际巡演,您认为中国戏剧如何从创新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
濮存昕:中国戏剧本身就是独特的,戏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语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真,不要刻意地去讨好或迎合他们的审美眼光。我们用自己的本真去真诚地表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本报记者:您认为阅读之于演员是一种基本素养吗?
濮存昕:当然,只有经过充分的阅读之后,才能提炼概括出角色最核心的部分,梳理出我们演绎这个角色的线条,编配主次关系。悟到这一条,这也是人生阅历教会我的。40岁以前我也不懂,哇啦哇啦念台词就演了。过了30年,重新去解读《哈姆雷特》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有新的发现的。20岁时候的阅读和60岁时候的重读,体会真是不一样,我成为导演之后尝试着做了3个戏,都是我认为过去自己没有演好的戏。
我非常感恩父亲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把书堆到了我面前,那时候,我13岁。而且父亲爱看报纸,我也跟着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虽然没学数理化,但是没缺阅读。
白纸黑字能够开发你的原始想象。对于演员来说,尤其要去仔细咀嚼文字,理解人物,与其产生共情,体会人内心的那种柔软。今天的短视频时代,长时间的阅读、大体量的阅读越来越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肤浅。我也看短视频,也离不开,因为短视频是不期而遇的。将来AI时代,一切都是定制的,你点击一下结论就有了,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在哪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情、品格审美。有头脑的人眼睛里是有光亮的,意识的光亮。
阅读的积累,会让你在大体量的文字中一下子就找到核心概念,所以说阅读力、理解力、概括力决定了演员的表现力。
本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表演艺术之路的?
濮存昕:下乡之后,我干了很多跟文化有关的杂活,比如出黑板报、刻蜡纸、编快板书。24岁回城,我选择了考文工团,要不然我就得去街道工厂做自行车链条。所以说,艺术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表演这个行业拯救了我。
我父亲是演员,我从小生长在剧院环境里。那些叔叔大爷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现在演戏演到难处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全是他们。他们告诉我,演戏可能得用这功夫劲,可能那样处理会更好。
回过头来看,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不把台词基本功拿住,就走不到这个行当的最上游。就北京人艺老演员们台词一丝不苟、不糟蹋一个字的那种演法,现在全国院团里都没有了。
我一直在特别地坚持这件事。台词基本功够扎实的话,心性可以让你再往上走;但基本功不够了,即使心存愿望,也是上不去的。很多人年轻时不重视基本功训练。这得让他们自己悟。我也是5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收拾”自己的嘴,跟孙道临、姚锡娟等老师学朗诵。演员的嘴上没有功夫,就啥都没有。现在孩子们缺师资也是一个问题,老师、导演对他们没有严格要求,都戴话筒表演,不用那么咬文嚼字。所以,演员能不能耐受住枯燥的台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地打磨自己,决定了他今后的路能走多远。
“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
本报记者:踏上辽宁这片黑土地,请谈谈您对辽宁戏剧的整体印象。如何做到让本土的地域风格既发扬光大,又不失本真?
濮存昕: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自己关起门来做文章,剧团就发展不好。你要用自己本真的技术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参与、共情。没有观众,什么派什么风格都没法建立。你必须跟观众交朋友,台上台下一起讨论。那个真实是真实感,而不是生活化的真实,是生活感的那种艺术表现力。
技术、风格,每个剧团都可以自己摸索。最重要的是,得把观众招到剧场里面来,精彩不精彩得看观众是不是买账。就像梅兰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像我者亡。意思是,你别像我,你就是你,但是你可以跟我学,学我的技术、腔调、品格。
我一直在思考,在表演行业有名有利算成功吗?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剧团只有建立起专业精神、专业标准,每个人都崇尚专业,杂事少了,钩心斗角少了,在艺术面前、在专业面前所有人都有虔诚的态度,这个剧团就容易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专业精神,每个人都是爷,那就麻烦了。专业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北京人艺老前辈们曾经有4句话——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生活积累,鲜明的角色形象,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是一个剧团要坚持的规矩、标准。
我们今天再谈发扬光大,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从事的是戏剧,你的深刻里必须还要有有趣的思想主题,让观众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思想是艺术承载的思想,要深刻而有趣。此外,要加上丰富的生活积累,到处都是生活。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生活,就是思想之间的互相给予。聊天、侃大山、竖着耳朵听社会小道消息、刷短视频,全都是生活。怎样每时每刻把这些信息归到艺术积累上来,一想,就马上想起那件事来。懂得举一反三,每打开一个积累,形象就出现了,聚合在一起。另外,角色形象老是标新立异,也不行,必须栩栩如生,既鲜明极了,又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恰当。那个东西是生动的,生长得像初生婴儿的嫩嫩的小屁股、打磨得像大理石似的那样光滑。完整的舞台演出质量,指的是包括售票员、引座员在内的剧院所有的门类、所有为演出服务的人员都做到了,像一棵菜一样地包着心,哪片叶都不能缺的完整性。每一行都有专业的标准,都是向心的。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最终就是观众说了算。不是票房说了算,票房是一个指标,但是进来的观众最有发言权。文艺要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以观众进剧场为宗旨。没进剧场说明你没水平,观众笑场说明你有问题,不是观众有问题。我们永远要心系观众,创作是最孤独的时候,但心系观众会让你不孤独。那时候,想的是我面对观众这样表演,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掌声。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就要有自己的自尊,要有自己的荣誉感。只有用真诚掏心窝子对待舞台对待作品对待观众,才会赢得尊重。
本报记者: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李白一演就是30年,以后还会继续上台表演吗?
濮存昕:我用排练、演出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不是对自己的救赎吗?我到今天也没有吃成脂肪肝,没有“三高”问题,70多岁了身体好好的,是一场场演出让我保持着好的生命状态。
这些天,在北京上演的《雷雨》,就是我们全新的一种解读,也是对曹禺先生1934年发表的初版剧本的开发。我很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对角色也有不断加深的理解,我希望能以自己对周朴园角色的演绎带观众找寻“曹禺密码”。
我很感恩观众帮我交学费,我演了四五十年,现在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演的叫啥呀,一点也不好,可是那时候观众就买票来看,所以真的要感恩。除了演戏我不会干别的,我也希望观众能再继续陪我一程。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刘俊英
摄
图片来源:人民网记者 刘俊英
摄

唐三的MBA之旅比比东的脚步不亦乐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8215
8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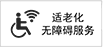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